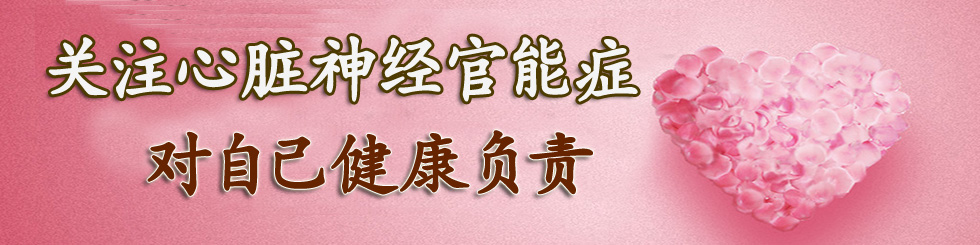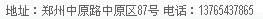|
身体疾病 个人的责任不只是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责任,许多医学证据显示身体的病痛会受到心理状态的影响。在身体疾病中,身心相互依赖的领域非常辽阔,基于篇幅所限,只能简单讨论癌症这个特殊疾病最近与责任相关的发展,以提供恰当的方向。 佛洛伊德在一九〇一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预示了压力与疾病相关的领域,他认为意外伤害并非出于意外,而是心理冲突的表现;他描述“容易受伤”的人会遇到特别多的意外伤害。在佛洛伊德之后两个世代的精神分析师发展出身心医学的领域,发现许多内科疾病都会受到病人心理状态的强大影响,例如关节炎、消化性溃疡、气喘、溃疡性大肠炎。现代生理回馈技术、静坐冥想、各种自动调节的机转引发大量研究兴趣,想了解人的控制和责任对自主神经系统掌管的身体功能有何影响(自主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的一个分支,长久以来被视为“不受意志控制的神经系统”)。 癌症之类的疾病长久以来被视为个体无法控制的疾病,但现在已把个人责任的观念运用到这类疾病的治疗。癌症一直被视为外来疾病的原型,它毫无预警地攻击病人,几乎无法影响其发病时间或病程。最近有大量宣传试图彻底改变对待癌症的态度,促使病人检视自己在疾病中扮演的角色。西蒙顿(O.CarlSimonton)是放射肿瘤学家,率先带领这项尝试,提出以心理为依据的癌症疗法。他的原理是根据当前的疾病理论,认为人一直都有癌细胞,但人的身体会抗拒这些细胞,除非抵抗力因为某种因素而降低才使人容易罹患癌症。有大量证据强调免疫系统和荷尔蒙的平衡受到影响时,会使人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西蒙顿推断:如果这项证据得到进一步支持的话,心理力量很可能就是影响癌症病程的主要因素。 西蒙顿的治疗方法包括每天的观想,病人先专注于一个象征影像,先想象癌症出现,然后观想身体防卫的某种象征影像打败癌症。例如,一位病人想象癌症是一堆生汉堡,然后想象白血球是一群野狗狼呑虎咽吃光汉堡。西蒙顿鼓励病人检视自己处理压力的方式,对一位癌症扩散开来的病人,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什么,使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就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存活时间;对于一个做出这么大的承诺,却忽视简单的研究以证实(或反驳)其主张的体系,我们必须抱持怀疑的态度。但是西蒙顿的方式教导我们在处理严重疾病时,责任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运用观想的病人,即使身体没有得到帮肋,也因为对疾病承担起更主动负责的态度,而常常在心理上得到帮助。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无助和低落的士气常常是治疗癌症病人时的主要问题。癌症可能比任何其他疾病都更容易产生无助感,病人觉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状况。罹患其他疾病的人(比如心脏病或糖尿病),有许多方式可以参与治疗,他们可以节食、服药、休息、遵守运动计划等等;可是癌症病人却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待,等到下一个癌细胞在身体某处冒出来,这种无助感常常被医生的态度扩大,医生在决定治疗过程时,常常不让病人参与决定,许多医生不愿意让病人知道病情,常常越过病人而与家属讨论关乎未来治疗的重要决定。 可是,如果西蒙顿的方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不能增加存活时间的话,是不是就是注定被戳破的谎言呢?还有什么治疗方法可以帮助那些无法接受西蒙顿的前提与方法的病人?我相信承担责任的观念可以为任何癌症病人提供治疗的着力点,即使是病情已到非常后期的人也可以适用。首先必须注意的是,不论人的身体环境如何(亦即逆境系数),都要对自己抱持的态度负责。我治疗罹患转移性癌症的病人时(他们的癌细胞已经蔓延到身体其他部位,无法以手术或药物治疗),特别注意病人对疾病态度的重要差异,有些人陷入绝望,心理上已经提早死亡,有些研究认为这种态度也会造成身体提早死亡。有些如我在第五章描述的人,能超越疾病,把即将来临的死亡当成催化剂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为自己的态度负责不必然代表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不过沙特认为要为自己的感受负责),而是对感受所抱持的态度负责。法兰克说明这一点时,讲了一个笑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犹太军医和非犹太裔朋友坐在狐狸洞口,这位朋友是爱挑剔的陆军上校。忽然枪声大作,上校揶揄地说:“你很害怕,不是吗?这可以证明亚利安民族比闪族优秀。”医生回答:“我当然害怕,可是谁比较优秀呢?亲爱的上校,如果你像我一样害怕的话,早就逃走了。” 处理癌症病人的治疗师可以针对病人的无助和绝望提供许多帮助。我和同事在癌症病人的支持团体中,发展出好几种方法来促进力量感和控制感。例如,癌症病人常常在医病关系中有无力感,觉得被当作小孩子对待,我的团体清楚地针对这个问题,有效地帮助许多病人在医病关系中承担起责任。病人描述自己和医生的关系后,团体成员会提出其他方法,以角色扮演让病人练习用新的方法在医生面前坚持自已的权益。病人学会要求医生给予足够的看诊时间,了解自已的病情(如果他想要的话);有些人则学会要求看自己的病历和x光片;还有人则会在合理的情形下,拒绝进一步的物,承担起最终的责任。 治疗团体有许多病人透过社交活动发展出能力感,许多人为癌症病人的权利请愿,为影响他们的政治议题而参选(例如义乳费用可以当报税的扣除额)。最后,如前所述,团体治疗师可以鼓励病人承担团体过程的责任,使他们重获能力感,病人越了解自己能引导团体以符合需要(事实上,引导团体本来就是他们的责任),就越能增加每个人在其他生活面也承担起责任。 责任与存在的内疚 试图促进病人觉察责任时,治疗师很快就发现治疗舞台会出现一种不请自来的现象,就是内疚,这是责任的黑暗阴影,常常阻碍存在心理治疗的过程。 存在治疗中,“内疚”的意义与其在传统治疗的意义有一点不同,后者是指一种做错事的感觉,是一种具渗透力而非常不舒服的状态,可以形容成焦虑加上自己很坏的感觉(佛洛伊德认为“内疚感和自卑感是很难区分的”。神经质的内疚和“实际”的内疚有一项区别,或是以马丁?布伯的话来说,就是“内疚”和“罪恶感”间的区别。 神经质的内疚来自反对他人、违反古今禁忌、违背父母或社会公断时所想象的过错(或是对小小的过错产生过大的反应)。“实际”的内疚则出自不利于别人的真正过错。虽然主观的不安经验是相似的,可是这两种内疚的意义和治疗是非常不同的:神经质的内疚必须处理觉得自己很坏的感觉、潜意识的攻击性,以及受处罚的愿望;而“实际”的内疚必须以实际或象征的方式适当补偿。 心理治疗的存在观点使内疚的概念增加许多重要的层面。首先,完全接受一个人行动的责任,会减少逃避的出口而扩展内疚的范围,不再能舒服地依靠如下的借口:“我不是故意的”、“这是意外”、“我没办法”、“我是出于无法抗拒的冲动”。于是实际的内疚及其在人际交往中的角色,会在存在治疗的对话中频繁出现。 可是,内疚的存在概念所增加的重要性,不只是拓展了“负责”的领域。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人感到内疚不只是出于对别人犯的过错,或是违反某种道德或社会的规范,也包括人对自己所犯的过错感到内疚。在所有存在哲学家中,先是齐克果,然后是海德格,两人把这个概念发挥得最淋漓尽致。重要的是海德格以同样的字(schuldig)来指称内疚和责任。他讨论传统对“内疚”的用法之后,说:“感到内疚同时也有负责的意思,也就是做为某件事的理由、作者,甚至是起因。” 所以人感到内疚的程度就像他对自己和世界负责的程度一样。内疚是“此在”(也就是人的存有)的基本部分:“内疚感最初并不是起因于亏欠感,刚好相反,只有在原本感到内疚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亏欠感。”海德格进一步引申这个主题说:“‘内疚’的想法有‘不’的特征。”“此在”—直不断形成,“一直落在其可能性之后”。所以内疚与可能性或潜在性是密切相关的,听到“良心的呼唤”时(也就是使人回头面对自己“真实”存有方式的呼唤),人总是会“感到内疚”,内疚的程度会大到使人无法实现真实的可能性。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还有许多人将之发挥得更彻底(也较不隐晦)。田立克的贡献与心理治疗特别有关,他在《存有的勇气》(TheCouragetoBe)讨论人想到失去存有时的焦虑,并区分出三种来源的焦虑,亦即失去存有会以三种主要模式威胁存有,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其中两种(威胁客观的存在——死亡,威胁精神的存在——无意义),第三种则与此处的讨论密切相关。失去存有会对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产生威胁(使我们体验自责的内疚与焦虑),进而威胁存有。田立克的话说得非常清楚: 人的存有不只是给予他,也对他有所要求。他要为存有负责;也就是说,他必须回答要使自己成为什么的问题。问他的人就是他的审判者,也就是他自己。这种情形会产生焦虑,以相对的措辞来说,就是内疚的焦虑;以绝对的措辞来说,则是自我排斥或自我谴责的焦虑。人被要求使自己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实现自己的命运。自我肯定的人在每一项道德行为中促成自身命运的实践,实现他潜在的可能。 田立克的观点认为人“被要求使自己成为应该成为的样子,实现自身的命运”,这句话引申自齐克果的观念,齐克果描述一种来自不愿意为自己的绝望。自我反思(觉察内疚)能缓和绝望,却不知道人仍然在一种更深形式的绝望之中。哈西德派的拉比苏斯雅(Susya)也有相同的观点,他在死前不久说:“当我到天堂时,他们不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是摩西?’而会问:‘你为什么不是苏斯雅?你为什么不成为只有你能成为的样子?’”兰克敏锐地觉察这些问题,他认为当我们限制自己,避免太过强烈或敏锐的生活或实践时,就会为我们未曾运用的生命而自觉内疚。 罗洛?梅认为可以从人与自身潜能的关系来了解压抑的概念,而潜意识的概念则可以放大到涵盖个人未得实现、受到压抑的潜能: 如果我们要了解某个人身上的压抑,就必须提出下列疑问:这个人与自身潜力的关系如何?他为什么选择或被迫选择不去了解自己知道的事,而又在别的层面知道自己其实知道?……所以不需要把潜意识想成不被文化接受的冲动、想法和愿望的储藏室,我认为潜意识就是人已知、却又无法或不愿实现的各种潜力。 罗洛?梅在别处把“内疚”(即存在的内疚)描述成“正向而有建设性的情绪……知道事物的现状与其应该成为的样子有何差别。”以存在的内疚(与焦虑)是符合心理健康的,甚至是心理健康所必须的。“当人否认自己的潜能,无法实现潜能时,他的状态就是内疚。” 这是由来以久的观念,认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潜能,渴望能加以实现。亚理斯多德的“圆满实现”(entelechy,或译为“元极”)就是指彻底实现潜能。七大原罪的第四项是懒惰,被许多思想家诠释为“无法把人所知自己所有能做的都在生活中实践的罪”。在现代心理学中,这是非常流行的观念,几乎每一位现代人本或存在理论家或治疗师的著作都会谈到。虽然它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自我实现”、“自我认识”、“自我发展”、“潜能发展”、“成长”、“自主”等等〉,但背后的观念很简单:每个人都有与生倶来的能力和潜力,而且原本就知道这些潜能。无法完全尽一己所能来生活的人,就会体验到被我在此称为“存在内疚”的深刻强烈感受。 例如荷妮成熟期的作品所牢牢依据的概念,就是人类在适合的情况下,会自然发展其内在潜力,就好比橡实会长成橡树一样。荷妮的重要著作《自我的挣扎》(NeurosisandHumanGrowth,直译为“精神官能症与人的成长”),副标题就是“为自我认识而奋斗”。根据她的观点,精神病理起于不良环境妨碍小孩的成长,无法认识自己的潜力,因而看不见自己潜在的自我,而发展出另一个自我形象——“理想化的自我”,把生命能量放在其上。虽然荷妮并没有使用“内疚”的说法,但她显然很清楚当人没有完成自身命运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她谈到疏离感(与真正的自己分裂),进而使人无视于自己真正的感受、愿望和想法。可是,人感觉到潜在自我的存在时,会在潜意识层面不断和“实际”的自我(就是实际活在世上的自我)比较。人的现状和人可能状况之间的落差,会产生大量的自我轻视,这是人必须用一生来妥善处理的问题。 马斯洛受到荷妮极大的影响,我相信他是第一个使用“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这个名称的人,他也相信人自然会实现自己,除非环境对发展太过不利,使人必须努力获得安全感,而不是努力成长(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采取“满足缺乏的动机”,而不是“成长动机”)。 如果人的本质核心被否认或压抑的话,就会生病,有时以明显的方式,有时以隐微的方式生病……这种内在核心非常纤细微妙,很容易被习性和文化压力战胜……即使它受到否认,仍然一直潜藏,不断要求得到实现……每一次与我们核心的疏远,每一个违反我们本性的罪过,都会记录在潜意识中,使我们鄙视自已。 可是人要怎么发现自己的潜力呢?人怎么在遇见它时认出它呢?人怎么知道自己迷失了呢?海德格、田立克、马斯洛和罗洛?梅都会同声回答:“透过内疚!透过焦虑!透过良心的呼唤!”他们一致同意存在的内疚是正向的建设力量,是呼唤人回归自己的向导。当病人告诉荷妮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时,她常常简单地回答:”你有没有想过要问自己?”人存有的核心是认识自己的。穆勒(JohnStuartMill)在描述自我的多样性时,谈到一种基本恒久的自我,他称之为“持久的我”(enduringI)。没有人把这一点说得比圣奥古斯丁更好,他说:“在我里面有一个人,比我本人更是我自己。” 一段临床写照可以说明存在内疚的向导角色。有位病人闪为严重的忧郁症和没有价值的感觉找我会谈,她已五十炮,结婚三十二年,丈夫是个心理非常不正常、心怀怨恨的人。她一生有多次考虑接受治疗,可是都决定不要,因为她担心自我检视会导致婚姻破裂,而她无法面对孤独、痛苦、丢脸、经济困难、承认失败。最后她因为过于无力,不得不寻求帮助,可是她的身体虽然在我办公室出现,却拒绝把自已交托给治疗,以致于我们毫无进展。有一天她谈到年华老去和恐惧死亡,而突然出现转折点。我请她想象自己接近死亡,然后回顾一生,描述她的感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后悔。”我问:“后悔什么?”她说:“后悔浪费了一生,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拥有什么。”“后悔”是她对存在内疚的说法,这是治疗的关键,我们在日后的治疗一直用它做向导。虽然在她面前是好几个月的艰苦治疗,可是她不再怀疑结局会如何,她确实检视自己(她的婚姻也确实破裂了),在治疗结束后,她能以“可能性”来体验生活,而不是后悔。 我在第五章谈过一个中年病人布鲁斯,他的治疗可以清楚说明内疚、自我轻蔑和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布鲁斯从青少年就对性爱十分着迷,特别是对乳房。他一生都很看不起自己,接受治疗是为了得到“抒解”,抒解焦虑、自恨,以及不断在内心啃啮他的内疚感。布鲁斯并不认为他是自己生活的作者,这种说法还算保守,为自己生活状况负责的观念,对他简直就像外国话;他觉得如此受驱迫、如此永无休止的恐慌,他就像卡夫卡一样觉得“能坐在角落呼吸已属幸运”。 在好几个月的治疗中,我们检视他的内疚和自恨,他为什么觉得内疚?他犯了什么过错?他自承犯了平庸、厌倦、琐碎的罪,而且在治疗中反复沉迷于吹嘘这些事:小时候偷了父亲的零钱,浮滥申请保险理赔,在申报所得税时做假,偷拿邻居早上的报纸,最重要的是和许多女人性交。我们依序详细探讨,而每次都重新发现自我的惩罚已超过他所犯的过错。例如,他讨论自己随便与人性交时,了解自己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对女朋友很好,并没有欺骗对方,对她们的感受也很体贴。虽然他从理性层面处理每一项“罪过”,了解自己是“无辜”的,对自己过于严厉,可是内疚和自恨一直没有减少。 他第一次瞥见责任是在讨论他对自信的恐惧时,虽然他的专业职务需要自信,可是他在公共讨论时无法好好代表自己的公司。反对或公开批评别人,对他是特别困难的事,最让他害怕的就是公开辩论。我问:“在那种情形下会发生什么事?最大的灾祸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暴露。”他害怕对手会毫不容情地大声宣读他一生可耻的性爱事件。他对乔伊斯(JamesJoyce)所著《尤里西斯》(Ulysses)中利奥波德?布卢姆的梦魇能感同身受,这个人因为私密的欲望受审判时,在法庭上陈列出许多小过错的证据而蒙羞。我对他最恐惧的事感到纳闷,他最怕的是暴露过去还是现在的性冒险呢?他回答:“现在的。我能处理过去的外遇,甚至可以大声告诉自己:‘那是过去的事,是我以前的作风。我现在已经改变了,我是不同的人。’” 逐渐地,布鲁斯开始听见自己的话,他的话其实是说:“我现在的行为,我此刻所做的事,才是我没有自信的来源,也是我轻视自己和内疚的来源。”布鲁斯终于了解他正是自恨的全部来源,如果他想要对自己有较好的感觉,甚至爱自已的话,就必须停止去做那些会令自己蒙羞的事。 不过,接下来出现更大的体悟。布鲁斯采取我在第五章描述的立场,首次选择放弃性征服的机会之后,开始渐渐改善。他在接下来几个月产生许多改变(包括预期会出现的阳痿期),不过他的强迫性逐渐消退,有所选择的感觉逐渐增加。随着行为的改变,他的自我形象也跟着大幅改变,产生极大的自信与自爱。治疗快结束时,布鲁斯逐渐发现内疚有两个根源,一个来自他看不起自己与他人相会的作风(我将在第八章深入讨论),另一个则是出于他对待自己时犯的过错。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肉欲,如性爱、乳房、性器官、交配、诱惑,和各种巧妙、放纵的性行为。布鲁斯在治疗发生改变之前,很少让心思自由奔驰、很少思考其他事情、很少读书(除非是为了让女人注意他)、很少听音乐(除了当成性爱的序幕),也很少与他人有真正的相会。布鲁斯形容自己去“像动物般一直活在垂挂两腿间热烈地来回戳刺的肉棒”。有一天他说:“假定我们有方法仔细研究昆虫,想象我们发现公的昆虫戳刺母虫喉中两块隆起物,用一生的日子想办法碰触这两片隆起物。我们会怎么想?为什么!这是多么奇怪的生活方式啊!生活当然有比碰触隆起物更重要的事。可是我就像那种昆虫一样。”难怪布鲁斯会觉得内疚,他的内疚就如田立克所说的,是来自他背弃、限制了生活,来自他的自我牺牲、拒绝成为他可以变成的样子。 把存在的内疚描写得最生动醒目的,莫过于卡夫卡。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主题就是拒绝承认与面对存在的内疚。《审判》一书从一开始就说“必然有人恶意中伤约瑟夫,因为他并没有做任何错事,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逮捕。”约瑟夫被要求认罪,他却宣称:“我完全无罪。”整本小说都在描述约瑟夫努力让自己自由地离开法庭。他从每一种可能的来源寻求帮助,却得不到协助,因为他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官方法庭。读者逐渐了解约瑟夫面对的是内心的法庭,在内心私密的深处。赫雪(JuliusHeuscher)注意到法庭被原始本能的东西玷污,比如法官的桌上都是色情刊物,法庭座落在贫民窟住宅的肮脏阁楼。 约瑟夫进入教堂时,一位神父向他说话,试图帮助他看见内心的罪,约瑟夫回答每件事都受到误解,然后辩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怎么能说任何人是有罪的呢?我们都只是平凡人,每个人都一样。”神父继续说:“可是每个犯罪的人都是这样说的。”再度劝他向内心看,而不是企图以集体的罪来消解自己的罪。当约瑟夫说自己的下一步是“得到更多帮助”时,神父生气地说:“你太热衷于寻找外来的帮助。”最后,神父从讲坛上高喊:“难道你就不能稍微看远些吗?” 约瑟夫希望从神父那儿得到逍遥法外的方法,“完全脱离法院管辖的生活方式”,他的意思是脱离自己良心管辖的生活方式。其实约瑟夫问的是,有没有方法永远不必面对存任的内疚?神父回答逃避的期望是一种“妄想”,告诉他一则“写在法律前言”的寓言,描述的就是”那种特别的妄想”,这是个沉痛的故事,谈到一个人和看门的守卫。一个乡下人恳求进入法律之门,在数不清数目的大门中的一个门前,守卫的人上前迎接,宣称他此刻还不被允许进入,这个人想从入口往里窥视,守卫警告他:“何不试试不顾我的准许就进去,不过,小心我是很有力量的。一间又一间厅堂,每—道门都有人看守,而且一个比一个更有力量,光是瞄一眼第三个守卫就会使我吃不消了。” 恳求者决定最好等自己得到许可才进入,他等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生都在门外等待。他老了,视力模糊,在死前躺下来时,向守门人提出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以前没有提出的问题:“每个人都努力得到法律,为什么这些年来,除了我以外,都没有别人要求进入呢?”守门人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因为他的听力也衰退了):“除了你以外,没有人可以进这道门,因为这道门是为你而设的。我现在要关门了。 约瑟夫并不了解这则寓言,直到死前还“像一条狗一样”寻找外来的帮助。从卡夫卡的日记来看,他本人最初也不了解这则寓言的意义。布伯指出,卡夫卡后来把这则寓言的意义彻底表达在笔记本上:“承认罪,无条件承认罪,门就会自动打开。它显现在世界之屋的内部,墙后就是污浊的反射。”卡夫卡描写的乡下人是有罪的,不只是没有活出应有生活的罪、等待许可的罪、没有把握生活的罪、没有只为自己而走进大门的罪,他有罪更是因为没有接纳自己的罪、没有以之为进入内心的向导、没有无条件认罪——这个动作会使大门“自动打开”。 书中并没有提到约瑟夫在判决有罪之前的生活,所以我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为什么有存在内疚。不过,赫雪在一篇精釆的病例报告中,谈到一位足以替代约瑟夫的病人T先生,他明显对自己犯下罪过: T先生因为无法呑咽而找我会谈,几周来他限定自己只能常常啜饮几口液体,结果体重掉了大约二十公斤。在生病之前,他的时间不是花在工厂(工作虽然有趣,但很固定),就是在家里,妻子虽然聪明,可是长期神经质、沮丧、酗酒,根本无法外出社交和娱乐。好几年前就已停止亲密的性爱,据称是出于双方同意,家中的活动仅限于阅读、看电视、妻子没有醉酒时的冷淡对话,以及偶尔有远亲来访。虽然他很受欢迎,口才又好,可是没有亲近的朋友,虽然他很想交朋友,却不曾大胆参加一些妻子无法加入的社交活动。虽然陷在这种僵化局限的世界里,他却灵巧地回避治疗师任何关于发展潜力、自由选择的建议。 虽然T先生的症状得到改善,可是两年的治疗并没有改变整体的生活方式。T先生就像约瑟夫一样,并没有倾听自己的声音,在治疗中一心避免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深入的检视,可是他坚持继续治疗,治疗师认为他的坚持表示潜伏的感觉,认为可能会得到更丰富的生活。 有一天,T先生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清晰地令他大为惊奇。虽然他没有读过卡夫卡的书,他的梦却与《审判》神似,这本书就像卡夫卡许多著作一样,都是起源自一个梦。T先生的梦太长,无法在此全部复述,不过,它是这样开始的: 我被警察逮捕,送到警察局,他们不告诉我为什么逮捕我,却嘀咕某种与“轻罪”有关的事,并要求我认罪。我拒绝时,他们威胁要以重罪起诉我,我回嘴说:“你要指控我什么就指控吧!”于是他们以重罪起诉我,结果我被判有罪,被关到农场监狱,根据一位警察的说法,这个地方专门关“非暴力重罪”的犯人。我被要求认罪时,最初感到恐慌,后来觉得愤怒和困惑,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可是逮捕我的警察告诉我,拒绝认罪实在很愚蠢,因为轻罪只会判刑六个月,而重罪至少会判刑五年,我被判了五到三十年! T先生和约瑟夫都受到存在内疚的呼唤,也都选择逃避呼唤,以传统的方式来解释罪,两人都宣称自己是无辜的,毕竟两人都没有犯下罪行,辩称“一定是搞错了”,各自努力说服外在的权威审判有误。可是存在的内疚并不是犯下某种罪行造成的,刚好相反!存在的内疚(其他的名称还有“自责”、“懊悔”、“痛悔”等等)是来自疏忽,约瑟夫和T先生都是因为生命中所没有做的事而有罪。 约瑟夫和T先生的经验对心理治疗师有非常丰富的意含,“内疚”是一种不安的主观状态,“因为自己不好而焦虑”的经验。不过,主观的内疚还有其他意义,治疗师必须帮助病人区分真实的内疚、神经质的内疚和存在的内疚。存在的内疚不只是一种不安的情感状态,也不只是需要处理和排除的症状,治疗师必须视之为来自内心的呼唤,如果加以注意,可以成为实现自我的向导。像约瑟夫或T先生一样有存在内疚的人,都违背了自己的命运,受害者是自己的潜在自我。要得到救赎,就必须把自己投入人类“真正”的使命,就如齐克果所说的“决心成为自己”。 北京好的治疗白癜风总共多少钱北京白癜风医院哪个比较好转载请注明原文网址:http://www.tknmb.com/mbyzl/36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