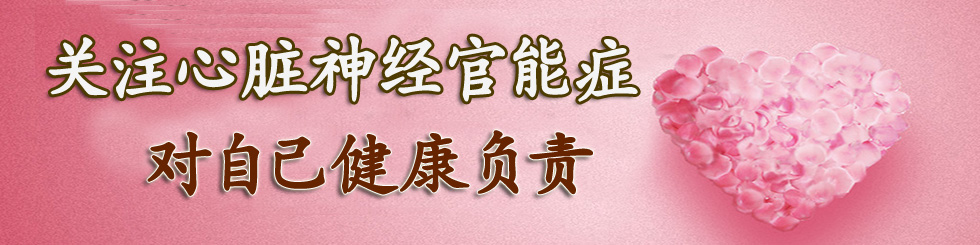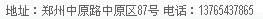|
在精神分析中,疏通(workingthrough)焦虑所有不同的单个形式之后,我们逐渐地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即基本焦虑是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尽管个体的焦虑可能由实际原因所引发,但是即使在实际情境中没有任何特定刺激的情况下,基本焦虑也依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较,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反抗。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或者它们可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国家中,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而在心理学领域也是一样的,焦虑的形式可能会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特定的刺激如何,焦虑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来源于一个共同的背景。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情境所作出的神经性反应,而这些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干扰。下述情况也许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出现。 一位45岁的妇女抱怨说自己在晚上老是心跳加速、焦虑不安,且伴有大量盗汗现象。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古道热肠、心直口快的女人。20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25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性生活也很令人满意,他们共同生育了三个孩子,这些孩子都发展得很好。她一直都很勤劳,并且善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脾气暴躁,性能力也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一切,没出现任何神经性反应。麻烦开始于七个月之前,当时,一个年龄与她相当、可以托付终身、值得喜欢的男人开始对她大献殷勤。结果,她开始对她年老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以及基本美满的婚姻关系,她完全压抑了这种情感。在几次访谈的帮助之下,她已经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情境,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性格神经症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与纯粹情境神经症案例(就像上文刚刚引用的案例)中个体的反应作一比较,能够更好地表明基本焦虑之重要性了。后者也出现在健康个体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一种冲突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冲突的存在以及这种冲突的性质,因此也就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种类型的神经症之间存在的一个明显差别在于,对情境神经症的治疗往往非常容易取得效果。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则往往必须在极大困难下进行,并因此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治疗的时间实在太长,以至于患者等不及治愈就退出了治疗;而情境神经症则相对比较容易治疗一些。一次关于情境的理解性讨论,通常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其他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来消除困难。①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与神经性反应之间存在着一种适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似乎并不存在。由于基本焦虑的存在,即使最轻微的刺激也有可能引发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外显形式的范围,或者说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的范围是无限的,在每一个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焦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与强度有所不同而已。我们或许可以大致地把它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助、被遗弃、受到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于一个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妒忌自己的世界之中的感觉。我的一个患者在她自发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达了这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是一个瘦小、无助、赤身裸体的婴儿,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种各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随时准备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通常发现,患者对于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有着相当高程度的意识。在偏执狂患者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身上;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的潜在敌意有着一种敏锐的觉察,这种觉察非常敏锐,以至于他们甚至很容易将他人对自己作出的善意表示,也当作包含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于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至少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对他整个一生会有怎样的重要性和意义。我有一位患者,她曾在梦中看到自己成了一只小老鼠,为了不被别人踩到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对她在生活中的实际表现作了最为真实的写照——她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害怕所有人,而且她还告诉我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一种针对所有人的基本不信任,被一种表面的信念(这种表面的信念就是,总的来说,人都是非常值得喜欢的)掩盖了起来,而且这种基本不信任还可能和与他人之间表面的、敷衍的友好关系同时存在;所存在的一种对于所有人的极度轻蔑,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来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所涉及的对象是人,但是它也可以完全摆脱某个人的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转变为一种受命运摆布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要让神经症患者本人认识这一点,即他的焦虑所针对的实际上并不是细菌之类,而是人,则往往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而且神经症患者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因为某些实际刺激而作出的适当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已变得从根本上对他人有敌意,不信任他们。 在描述基本焦虑对神经症患者而言的意蕴之前,我们必须先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难道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意的态度(被描述为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具有(尽管很可能程度相对较轻一些)的“正常”态度吗?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这个词是从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在德国哲学与宗教语言所谓的生之苦恼(AngstderKreatur)中,基本焦虑确实有一种正常的推论结果。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些比我们自身更为强大的力量,如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意外事故等面前,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很无助的。我们在儿童期的无助中第一次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这种认知会在整个一生中都伴随着我们。这种关于生(Kreatur)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也包含着面对更大力量时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不过,如果“正常”一词是从对我们文化而言为正常这个意义上来加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这么说:一般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其生活不是过于闭塞的,经验通常能使一个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为保守,更善于提防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即通常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为懦弱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会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而如果他不诚实,他就会在他人身上更为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简言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非常相似的态度。不过,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区别:健康、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的弱点感到无助,在他身上也不会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而在基本的神经性态度中,我们发现了这种倾向)。而且,他依然能够给一些人以许多真诚的友谊和信任。或许,这样一种事实就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区别,即健康人是在他能够整合那些不幸经验的年岁里遭遇着大量的不幸经验的;而神经症患者是在他无法掌握的年岁里遭遇了那些不幸经验的,而且由于无助,他对这些不幸经验作出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对于个体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态度而言,有着特定的意蕴。它意味着,情感隔离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那么这种隔离就会更让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对自信心之基础的一种削弱。它播下了一种潜在的冲突的种子,因为一方面神经症患者想要依赖他人,而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这么做,因为他对他人有着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它意味着,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个体感觉到了一种想要把所有责任都放到他人肩上的愿望,感觉到了一种想要受到保护、受到照顾的愿望,但是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有着太多的不信任,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必须彻底。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试图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对抗焦虑的强有力的保护手段。格言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根据是否涉及特定的人或制度而粗略地作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仪式的顺从中,在对某个权威人物之要求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遵从这些规则,或者顺从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些态度可能会以不得不“听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听命”的内容会随着所要顺从之要求或规则的不同而不同。 当这种顺从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呈现出更为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所有人的潜在愿望,并且避免任何有可能引起愤怒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的所有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让自己受到虐待而不自卫,并且随时准备不加区分地帮助他人。偶尔人们也会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焦虑是上述行为的基础,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的崇高,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愿望。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都是:如果我屈服,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来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至于他在生活中的安全感都依赖于此,那么,他就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而且这大体上还意味着对于他人愿望的顺从。不过,通常情况下,个体都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刻板的顺从,才能获得安全感。在他们身上,焦虑非常强烈,对爱的不信任非常彻底,以至于爱的可能性完全被他们拒于门外。 第三种保护自己对抗焦虑的尝试是通过权力实现的——试图通过获得实际的权力、成功、获得他人钦佩、智力优势或占有某物,来获得安全感。在这种为获得保护而作出的尝试中,格言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不过,通过从世界中退缩出来也同样可以实现这种保护。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或过着完全隔离的生活,而是说当他人对自己的内在需要或外在需要产生影响时,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通过诸如聚敛财物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占有的动机完全不同于为了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且对占有物的使用同样也是不同的。只要囤积占有物的目的是为了独立,那么通常情况下,占有者都会感到非常焦虑,以至于他们无法享用这些占有物;而且他们通常都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占有的唯一目的是预防所有万一发生的不测事件。另一种服务于同一个目的的、使自己在外在需要方面独立于他人的手段是,将个人的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 内在需要方面的独立,可以表现为试图使自己脱离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样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伤害到自己或者使自己失望了。它意味着压抑个人的情感需要。这种独立的表现之一就是一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的态度,包括对个人自己也满不在乎,这样一种态度通常见于知识分子圈中。对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是相互矛盾的。 这些退缩手段,与屈从或顺从的手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都涉及了对个人愿望的放弃。但是,在后一种类型中,放弃个人愿望是为了“听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前一种类型中,“听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个人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独立,不依赖于他人。这里的格言是:如果我退缩,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 为了评价各种为保护自己免受基本焦虑而作出的尝试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它们的潜在强度。它们不是由一种想要满足快乐或幸福欲望的愿望所促成,而是由一种安全需要所促成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它们无论如何都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拒。经验表明,诸如对某种野心的追求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与性冲动一样强大,甚至更为强大。 只要生活情境允许这样做而不会招致任何冲突,那么排外地或片面地追求这四种手段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会有效地带来个体所想要的安全感——即使这样一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导致整个人格的贫瘠。例如,在一种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顺从各种传统形式的文化中,一个遵循顺从路线的妇女,可能就会获得安宁和许多次级性满足。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主,其结果同样也可能是获得安全感和功成名就的人生。但是,事实上,对于某一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通常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他所设定的要求非常过分,考虑非常不周,以致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之中。更为常见的是,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通过几种方式(而且这几种方式是互不相容的),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患者同时也可能被强迫性地驱使着去控制所有人而又希望被所有人爱,去顺从他人而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去疏远他人而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为常见的动力中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尝试,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更为详细地讨论这两种尝试。 从原则上说,我所描述的神经症结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不矛盾。弗洛伊德认为,大体而言,神经症是本能驱力和社会需要(或者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表现)之间冲突的结果。然而,尽管我也同意这一点,即个体努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一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限制,也就是说,导致对种种欲望的简单压制或压抑,或者用更为一般的话说,导致事实性的痛苦。只有当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试图缓解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了种种防御倾向(这些防御倾向尽管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但它们却是彼此互不相容的)时,神经症才会产生。 赞赏 长按北京白癜风费用大概多少怎么预防白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