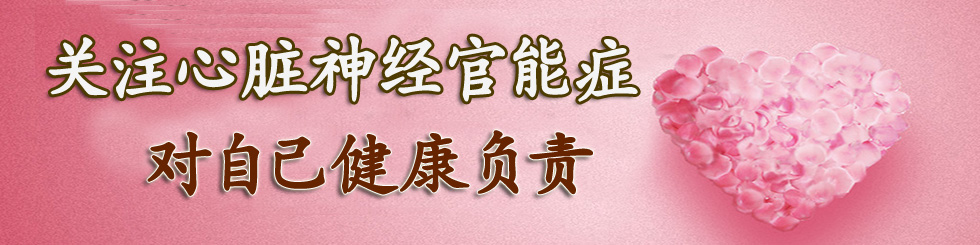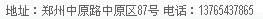|
.恐惧型神经症phobicneurosis 见:焦虑型歇斯底里。 .创伤型神经症traumaticneurosis 指一种神经症类型,其中症状的出现紧接于一情感冲击之后,此情感冲击通常与一种令主体感到生命受威胁的情境有关。创伤型神经症的征象为受到冲击时产生极度焦虑的危象,此种危象可能引起躁乱、木僵或心神错乱等状态。由其后期的演变(通常发生于一段不定的间隔之后),我们可以简要地区分以下二例: a)创伤的作用犹如启动元素,触发一个已存的神经症结构。 b)创伤在症状内容本身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如对创伤事件的反复思索、重复出现的恶梦、睡眠紊乱等),症状仿佛是想要“连结”并弭除反应掉创伤的一种重复的企图;像此种“固着于创伤”的现象,会伴随对主体行为大致普遍化的禁制。 佛洛伊德以及精神分析师们所谓之创伤型神经症,通常是指定义b的临床病情。 创伤型神经症一词在精神分析之前便已存在①,并且持续在精神医学中以各种不同方式被使用。这些用法的不同,在于创伤观念所具的歧义性,以及该歧义性所容许的理论选择之分歧。 创伤最早是一种身体性的观念,指“……由一种伤害作用高于所接触组织或器官之抵抗力的机械因素在瞬间意外造成的损伤”;根据皮质表层是否破坏,创伤又可分为伤口及挫伤(或内伤)。 但在神经精神医学上,创伤用于两种非常不同的词义: 1)将创伤的外科观念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此一特殊例子上。创伤的后果可能是从神经物质的明显损害一直到假设性的显微损害(例如“震荡”的观念); 2)以隐喻的方式将创伤观念转移到精神层面,形容所有使个体精神组织突然受到破坏的事件。对精神医师而言,大部分导致创伤型神经症的情境(意外、战斗、爆炸等),在实践层面上均构成一个诊断的问题(神经是否受损?)。而在理论层面上则留有很大自由,使他们得以根据个人的理论选择来评估障碍的最终成因。某些论者甚至将创伤型神经症的临床病情归类于“脑颅创伤”架构下(见:精神创伤)。 若局限于精神分析所考虑的创伤场域,则可就两个相当不同的角度理解创伤型神经症一词: I.参照佛洛伊德所谓引发神经症的“互补系列”,应考虑两种互为反比的因素:先天素因与创伤。我们于是可列出一系列不同等级的案例:包括因主体对所有刺激或某种特别刺激的低忍受度,以致任何轻微事件均可能成为发病因素,以及一个客观上异常剧烈的事件突然扰乱主体平衡的例子。 对此我们说明如下: 1)创伤的观念在此成为纯粹相对的观念; 2)创伤/先天素因的问题,倾向于与现实因素及已存冲突的各自角色的问题混淆(见:现实型神经症); 3)在一些明显是由一重要创伤造成症状出现的病例上,精神分析师致力于从主体历史中寻找仅是被事件所催化之神经症冲突。应注意,以此种观点作为依据,创伤(战争、意外等)所引发的障碍经常都类属于古典传会型神经症上可见的障碍; 4)在此面向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在事件正好实现主体受抑制的欲望、导演其无意识幻想的案例。在此类案例中,被引发的神经症均具有反复思考、重复的梦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它类属于创伤型神经症; 5)在同一思想路线上,人们甚至认为创伤事件的发生与一种特殊的神经症素因有关。某些主体在畏惧的同时,也仿佛无意识地找寻创伤情境。根据费倪雪(Fenichel),他们藉此重复一个儿童期创伤,以便予以弭除反应: “……自我欲求重复,以便化解一种痛苦的紧张,但重复本身便是痛苦的……。病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重复所力求之‘迟来的控制’从未达到……,因为每一次重复都带来一个新的创伤经验”。费倪雪认为,这些被称为“恋创伤癖”(traumatophiles)的主体,是“创伤型神经症与精神神经症组合”的典型例子。此外应注意,关于这点,引进“恋创伤癖”一词的亚伯拉罕(K.Abraham)也认为,童年的性创伤本身与一个己存的恋创伤癖素因有关。 Ⅱ.可见精神分析研究如何置疑创伤型神经症的观念:精神分析一方面强调创伤事件与主体忍受能力之相对性,另一方面,将创伤经验置于主体的历史与特殊组织中,由此质疑创伤事件的决定性功能。在这个角度上,创伤型神经症的观念将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描述性的初步接近,禁不起对相关因素更深入的分析。 然而就疾病分类与病因的角度而言,难道不应给予此种神经症——其中,创伤基于其性质与强度,远较其他致病因素更为重要;且与精神神经症相比,其中运作的机制与症状学也相对地较为特定——保留一个特殊地位? 这似乎正是佛洛伊德在《超越快感原则》一书中所揭橥的立场:“创伤型神经症的症状病情类似歇斯底里,因为它亦具有大量类似的运动性症状;但一般而言,它在以下几点均超出歇斯底里的范围:它具有剧烈升高的主观痛苦征兆——约似疑病症或忧郁症——以及心灵功能上广泛的一般性衰弱与紊乱特征”。当佛洛伊德论及创伤型神经症时,他强调创伤兼具身体(生命体受至到“震荡”[Erschütterung]所引起的刺激的汇集)与精神(Schreck:惊吓)的特征。佛洛伊德认为此种惊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危险情境的状态”——是创伤型神经症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突然涌入并且危及主体之整体性的刺激汇流,主体既无法透过一个适当卸除,亦无法透过一种精神工作予以回应。由于被其链接的功能所淹没,主体强制地重复创伤情境——特别是以梦的方式②——以便试图予以连结(见:重复强制;连结)。 然而,佛洛伊德也不忘指出,创伤型神经症与传会型神经症之间可能存有共通点。正如《精神分析纲要》中下列文字所示,他使创伤型神经症的特殊性成为一个开放性问题:“或许所谓的创伤型神经症(由一个过度剧烈的惊吓或身体的重度震荡,如火车对撞、遭土石掩埋等)是个例外;但它们与儿童期条件的关系截至目前仍未受到研究”。 .对象(客体)object 精神分析以三个主要面向来思考对象的概念: A)与欲力的关系:在于对象并且凭借对象,欲力试图达成其目的;亦即某种类型的满足。所涉及的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部分对象,也可能是一个真实或是幻想的对象。 B)与爱(或恨)的关系:此处的关系,是与整个人、或是与自我的审级,以及与本身被视为一整体的对象(人、实体、理想等等)之间的关系;对应的形容词为“对象性的”。 C)从哲学与认识心理学的传统意义下,与知觉与认识主体的关系:它是任何以固定、不变特征去自呈之物。不论个体的欲望或意见为何,这些特征都理所当然地可藉主体的普遍性而辨认(对应的形容词为“客体的”)。 在精神分析著作中,对象一词或者单独出现,或者出现在像是对象选择、对象爱、对象的失去以及对象关系等可能会使非专业读者困惑的许多用法之中。对象在可模拟为该词在古典语言中所被赋予的意义(“我狂热、幽懑之对象,爱恋对象”等)下被理解。对象一词不应令人联想到“物”、以及无生命且可被操控的物体之概念,如同它通常对立于有生命存在与人的概念。 Ⅰ.对象一词在精神分析中的这些不同用法,来自于佛洛伊德对欲力的构思。从佛洛伊德一开始对欲力的概念进行分析时,他便将对象与目的区分开来:“我们引进两个词汇:我们所谓性对象,是指发出性吸引力之人,欲力所推动的行为为性目的”。佛洛伊德在其所有著作中始终保持此对立,尤其在他对欲力所作的最完整定义中又重新将之确定:“欲力的对象,是那在此或藉此欲力得以达到其目的之物”;同时对象被定义为视满足而定的手段:“它是欲力中最多变之物,原先并非与之连系在一起,而只因它具有使满足成为可能的能力,才被分派在前者之上”。对象的偶然性这个佛洛伊德主要且持续的论点,所意指的并非无论何种对象都可以满足欲力,而是(时常带有独特特征的)欲力对象乃是由每个人的历史——特别是儿童期的历史——所决定。对象在欲力中最不受体质所决定。 此种构思并非未引起争议。藉由参考费尔本(Fairbaim)所作的区分,这些问题的位置可被概述如下:力比多究竟是快感的追求(pleasure-seeking)、抑或是对象的追求(object-seeking)?对佛洛伊德而言,无疑地力比多——即使很早就承受某种对象的印记(见:满足的经验)——最初藉由对适合每个动情带的活动形态而言最短的路径,完全朝向满足:紧张的解除。尽管如此,目的与对象的性质与“命运”之间紧密相关这个被对象关系理论所强调的看法,对佛洛伊德的思想而言并不陌生(关于此点的讨论,见:对象关系)。 此外,佛洛伊德对于欲力对象的构思,乃是立基于对性欲力的分析上,于《性学三论》一书中建构。然而对于其他欲力的对象,特别是在佛洛伊德第一二元论的架构下,自我保存欲力的对象,他的概念为何?就后者而言,对象(如食物)更明确地是为生命需求的坚持要求所殊化。 然而,性欲力与自我保存欲力间的区别,不应导致对其对象的地位作一种过于僵硬的对立:在一者中具有偶然的性质,在另一者中被严格决定,并被生物性地界定。况且佛洛伊德指出,性欲力藉由依附于自我保存欲力之上运作,这明显地表示后者为前者指出朝向对象之路。 藉助依附这个观念,人们得以厘清与欲力对象有关的复杂问题。若以口唇阶段为例,用自我保存欲力的语言表达,对象是提供营养者;以口唇欲力的语言而言,它是体内化之物,带有体内化所包含的整个幻想向度。对口唇幻想的分析指出,体内化此种活动可针对食物对象之外所有其他对象,这因此定义了“口唇型对象关系”。 Ⅱ.对象的概念在精神分析中并不只藉由与欲力的关系而被暸解——若后者的运作真的可在纯粹的状态下被掌握的话。它同时也指任何对主体而言作为吸引的对象、爱恋对象者,最通常是指一个人。唯有分析研究方能发现,远远超过自我与其爱恋对象的此一总体关系,欲力在其多形,其变异,以及其幻想相关物中的作用本身。在佛洛伊德最早分析性与欲力的观念时,欲力对象与爱恋对象彼此如何衔接的问题尚未明显出现,并且不可能存在;实际上,第一版的《性学三论》以存在于儿童性(sexualitéinfantile)的运作与后青春期性的运作两者间的主要对立为其轴心。前者被定义成基本上是自体情欲的,在佛洛伊德这个思想阶段,所强调的重点不在于它与异于身体本身的(即便是幻想的)某一对象间之关联这个问题上。欲力在儿童那里被定义为部分的,相较下更是由其满足模式(就地的快感、器官快感),而非根据其所针对之对象类型而定。一直要到青春期,一种对象选择——其“预兆”与“雏形”可在童年中被发现——才介入,这使性生活不但得以统一,也同时决定性地朝向他人。 我们知道,在到年间,儿童期自体情欲与青春期对象选择间的对立逐渐减弱。一系列力比多的前生殖阶段被描述,这意味一种完全独特的“对象关系”模式。自体情欲此一观念所可能导致的歧义(自体情欲可能会被理解成意味主体起初忽视所有外在对象,不管它是真实或幻想的)亦消散不见。部分欲力其作用定义了自体情欲——之所以被称为部分的原因,乃是因为其满足不仅与某特定动情带,并且与被精神分析理论称作部分对象之物有关。佛洛伊德在《论欲力移位,特别是在肛门情欲中》强调,介于这些对象之间建立若干象征等式,这些交换使欲力生命经过一系列变形。部分对象问题的效应,拆解了相对未分化之性对象的概念在佛洛伊德思想初期可能具有的概括性。事实上,我们的确会被导向将真正的欲力对象与爱恋对象两者拆分开。前者根本上被定义为可以为相关欲力获得满足。这对象可以是一个人,然而这并非是必要条件,因为满足显然可由身体的一部分所提供。由于对象取决于满足,强调的重点便因此在对象的偶然性上。至于对爱恋对象的关系,它与恨一样,诉诸另一对词组:“……爱与恨的关连不适用于欲力对其对象的关系上,而应专门用于整个自我对对象的关系上”。关于此点必须注意的是,就术语的观点而言,虽然佛洛伊德强调对部分对象的关系,但他仍将对象选择的说法,专门用来指人对其爱恋对象的关系——这些爱恋对象本身本质上是整个人。 由部分对象——欲力对象,以及主要地,前生殖对象——与整体对象——爱恋对象,以及主要地,生殖对象——之间的对立,人们或许因此会从心性发展的发生论角度得到下列推论:藉由将其部分欲力逐渐整合进生殖组织中(生殖组织逐渐增强考虑对象性质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及其本身的独立性),主体由部分对象过渡到整体对象。爱恋对象不再只是欲力的相关物,注定要被消耗。 尽管欲力对象与爱恋对象的区分,不论其影响是如何地无可置疑,然而并不必然包含上述的构思。一方面,部分对象也可被视为是性欲力不可被化约、无法被超越的一极。另一方面,分析探讨也指出,整体对象远非某种最终成果展现,它从未缺少自恋蕴涵,在其组成原则里,所介入更多的是各种不同部分对象一种沉淀化为以自我为模型的形式①,远甚于这些部分对象的精巧综合。 介于依附型对象选择——在其中,性自我取消以便利于自我保存的功能——与自恋型对象选择——复制自我;介于“哺育的母亲,保护的父亲”与“人们是,曾经是,或是欲成为之人”,像《自恋导论》一类的作品使爱恋对象的确切地位很难被确定。 Ⅲ.最后,精神分析理论也参考传统哲学意义下——亦即,与知觉与认识主体的概念相连——的客体概念。当然,这必然会产生介于以如此方式构思的客体,和性对象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若人们构想欲力对象的演化,且特别是,若此演化导致一个生殖爱恋对象的构成——其定义为具丰富性、自主性与整体特征——则人们必然认为此对象与知觉客体的逐渐形构有关:“对象性”(objectalité)与客体性(objectivité)并非无关。有鉴于此,许多论者致力于调和精神分析关于对象关系演化的构思,与认识发生心理学的与件,或甚至拟定出“精神分析的认识理论”梗概(关于佛洛伊德所提出的若干指示,见:快感,自我/现实-自我,现实的测试)。 赞赏 长按北京去哪里医院看白癜风最好皮肤病治疗最好的医院
|